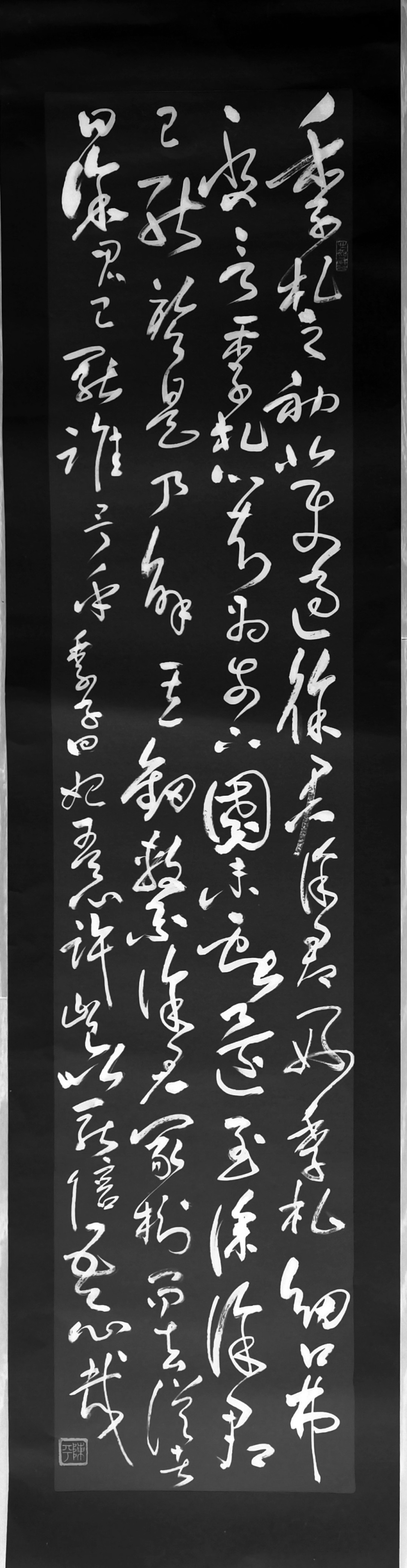
《诗经》与爱情
陈平
《 诗经》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,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,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(前11世纪至前6世纪)的诗歌,共311篇,其中反映男女爱情的诗多种多样,有幽会时亲昵的《邶风·静女》,有写情侣春游时欢快的《郑风·溱洧》,有写两情野合欢娱的《召南·野有死麕》,有写饱含思念的《王风·采葛》,有写情女想情郎的《郑风·子衿》,有写情侣闹别扭的《郑风·狡童》,有写意中人不可求而空恨的《周南·汉广》,也有写表现意中人难以亲近的《秦风·蒹葭》,有写失恋苦涩的《召南·江有汜》,更有写遭到家长干涉的《郑风·将仲子》,还有反抗家长干涉的《王风·大车》等等,等等。可说是举不胜举,丰富多彩。
从这些列举可以看出,《诗经》广泛反映那时代男女爱情中的幸福快乐,挫折痛哭,让我们体会出充满坦诚、真挚的情感流露,这些情诗大多是用女性的口吻来写的,她们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与热烈,也许就是那时民风的古朴与使然。
如《郑风·褰裳》中,子惠思我,褰裳涉溱。子不思我,岂无他人?狂童之狂也且! 子惠思我,褰裳涉洧。子不思我,岂无他士?狂童之狂也且。短短几句对话便把情人相戏的情景,淋漓尽致展现在我们的面前,给人产生民生纯朴感觉。
除了以女性口吻来写外,以男性口吻写的诗也能体现女性在恋爱中示爱的情趣,如《邶风·静女》这诗,便以男子口吻写幽期密约的乐趣:静女其姝,俟我于城隅。爱而不见,搔首踯躅。 静女其娈,贻我彤管。彤管有炜,说怿女美。
他爱的姑娘,按照约定在城角楼等他,也许为了逗着玩,她把自己隐藏起来,他来时见不着她,急得搔首踯躅。
等到他发现姑娘已经来了,而且情意深长地给他带了一些礼物便大喜过望。幽静的城角,情侣来调情,一派温情脉脉的场景,让爱情自然流露充满甜蜜,然而现实却给他们感情增加了许多束缚。
在那个时代,男女婚姻已有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的参与,不再是完全的自由的了。《礼记·曲礼》中讲,男女非有行媒,不相知名,《仪礼·士昏礼》中的昏礼下达,纳采用雁。《礼记·坊记》中有伐柯如之何?匪斧不克。娶妻如之何?匪媒不得。艺麻如之何?横从其母。娶妻如之何?必告父母。可见那时对男女之情已经有限制了,对女性而言受到的束缚更多,既不愿舍弃情郎,又不敢违反父母的命令。
《郑风·将仲子》就描写了一位为情所困的女子;将仲子兮,无逾我里,无折我树杞。岂敢爱之,畏我父母。仲可怀也,父母之言亦可畏也。将仲子兮,无逾我墙,无折我树桑。岂敢爱之,畏我诸兄。仲可怀也,诸兄之言亦可畏也。
将仲子兮,无逾我园,无折我树檀。岂敢爱之,畏人之多言。仲可怀也,人之多言亦可畏也。
《将仲子》里的这位女主人公害怕的。正是这些礼教,对于仲子的爱和父母、诸兄及国人之言,也成少女心中纠缠不清的矛盾,一边是自己所爱的人,另一边是自己的父母兄弟,怎么办呢?几多愁苦,几多矛盾,少女的心事又怎能说清呢?
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中写道,丈夫生而愿为有官,女子考而愿为有宗,父母之心,人皆有之。不待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,钻穴隙相窥,逾墙相从,则父母国人皆贱之。
《诗经》中对女性爱情的描写真实自然,用“思无邪”来形容里面的感情恰到好处。《诗经》作为一部古代的诗歌总集,里面记载的诗歌并非一时一地之作,从这些爱情诗中我们也可看出,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,民间的风俗是不同的。
对这些诗歌的具体年代,我们不甚清楚,但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,古代婚姻恋爱风俗也是由开放到保守的过程,各诸侯国和不同地区的风俗也有所差异。
如评注者常说“郑声淫”,从现在的观点来看,其实郑国的诗歌多是大胆表露男女之情,比其他地方更热烈而已。而从《褰裳》到《将仲子》同为《郑风》却能看到差别,前者更加开放,后者却顾虑重重,这也许是因为时间不同,也许是因为作者身份不同,但总体来看,当时的婚姻制度非后来封建时期规定严格,较之还是相对自由的。
《诗经》中的爱情诗,为我们记录了中国古人美好的爱情生活,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的风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。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,也是诗歌永恒的主题,可谓几多甘甜几多辛酸;《诗经》用纯朴的语言酿造了先人生活中美妙的酒浆,品之既高雅又朴实,让当代诗人很难以与之嫓美,即使出过几本书仍然望尘莫及。
